我不是伊斯蘭的路德,專訪:伊莎德?曼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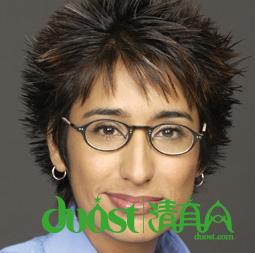
伊莎德?曼吉(Irshad Manji)的短發根根精神抖擻,嘴里蹦出來的詞兒也個個擲地有聲。她紐約的寓所安裝了防彈玻璃,她不使用手機以免不法之徒跟蹤到她的位置。她的大作《伊斯蘭問題》(The Trouble With Islam Today,2004)在中東國家遭到了全面禁售,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卻暢銷不衰,該書的波斯語和烏爾都語電子版在互聯網上也達到了五十萬次的下載量。近期她前往華盛頓為奧巴馬政府的穆斯林政策建言,并敦促女性組織打擊以宗教之名對女性人權的侵犯。關于她的紀錄片《信者無畏》(Faith Without Fear,2008)也被提名艾美獎。
活力四射,見解非凡,談吐犀利而富文采,剛在紐約大學獲得教職的曼吉絕對讓你一見難忘。她一上來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的伊斯蘭已經徒有虛名,而千百萬穆斯林卻因它而被剝奪作為人的基本權利。沒有第二個人敢像曼吉這般口無遮攔,如此尖銳的評價,即使對于改革派的穆斯林來說,恐怕也過于直白。但是,曼吉似乎生來就無法和她不能茍同之人相安無事,對那些聲稱“要么讓穆斯林皈依基督、要么就把他們趕回中東老家”的基督徒來說,曼吉同樣是個不討好的人物。
是什么,讓這個成長于溫哥華郊區的穆斯林女子在她纖細的身軀里埋藏了如許之多的能量?她為何,能在伊斯蘭信仰變得極具爭議的當下,無所顧忌地發出宗教改革的領軍之聲?

1972年,四歲的伊莎德?曼吉隨父母作為遭到烏干達當局驅逐的南亞移民,遷居加拿大政治避難。十歲上,眼見父親把母親往死里打,小曼吉企圖報警,卻被父親用一把菜刀逼上了房頂。孤單無援的她在房頂上聽到了真主的聲音,真主告訴她:你應該為眼下的生活感到慶幸,因為你至少逃離了生靈涂炭的烏干達,而在加拿大,會有人愿意傾聽你的遭遇;但是,作為一個民族,你們的故事遠遠沒有講完,而你,作為個體,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為你是這個宏偉故事的作者之一。
十四歲,曼吉被趕出了周六的宗教學校,只因為她的“十萬個為什么” 令人無比惱火——為什么女孩不能帶領禱告?為什么我不能用自己熟悉的語言來閱讀《古蘭經》?...照說被開除的她當時滿可以從此放棄信仰,可曼吉偏偏倔得很,她非但沒有放棄伊斯蘭,相反,她還深思熟慮地總結了信仰在自己生命中的地位:信仰和當代世界的物質主義構成一種張力,信仰讓人保持思考的狀態,從而避免滑向任何的極端主義,無論是女性主義的極端,還是國家主義的極端,或者文化多元主義的極端。“神在我的意識中從來是一位不安的棲居者,信仰讓我只向神表達謙卑;在這個千變萬化、流轉不息的時代,這種謙卑彌足珍貴。”
在當地圖書館,曼吉饑渴地查閱關于伊斯蘭的文獻;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習思想史的曼吉榮獲省長頒發的“最佳人文畢業生”獎章;她先在一份女性主義報紙當編輯,接著又在“酷兒TV”節目當主持人和制片人;二十歲上她邂逅了第一個女朋友,她隨即向母親出柜,此后便一直對自己的女同身份直言不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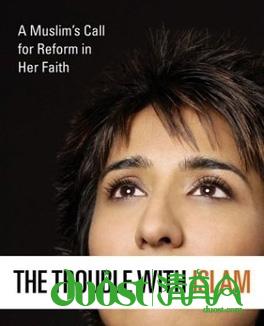
同性之愛被幾乎所有的穆斯林領袖所不齒,而曼吉那位打著信仰的旗號虐待妻女的父親對此更是鄙夷有加,但是,曼吉并不認為是性傾向促使她產生了改革伊斯蘭的想法,她堅稱,伊斯蘭的改革,是理性思考所導致的符合邏輯的結論。
“總有人認為我對伊斯蘭的詰難源自我童年的經歷”,曼吉不依不饒地說,“大錯特錯!這些人太抬舉我的童年了。在過去的百年當中,因伊斯蘭之名而遭受迫害的穆斯林人數遠遠多于遭到異族迫害的穆斯林人數。難道這也是我童年經歷的一部分?”
對于曼吉來說,童年早已是被笑忘的過往。她的父母最終離婚,她此后再沒見過父親。她說:“曾經也恨過他,但我總不能一輩子活在仇恨里,所以,我做了一個決定,對他,我且疏離、漠視,最后方能悲憫視之。”
而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水火不容的穆斯林和同性戀的雙重身份,在曼吉這里卻全無困擾。她承認,早年也曾納悶,真主為何讓她生為女同志、卻又在古蘭經里宣布仇視同性戀?但在著述當中,曼吉非常有分寸地把這個問題一筆帶過,“因為我覺得討論這個沒啥意思,反正我已經處之泰然了。”
曼吉更重要的論點在于,伊斯蘭需要重拾它的批判性思考的傳統,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沉湎于對創教的光輝歷程的追憶。伊斯蘭教義中本來存在的“伊智提哈德”( ijtihad,意為 “獨立判斷、盡力而為”)正是這樣一種富于智識激情的傳統,它可為伊斯蘭教改革自身、適應新世紀提供參考。

真正讓曼吉下定決心成為一個宗教改革主義者的,是她早年在一家電視臺工作時的一件事。有一天老板放了一則剪報在她桌上,報道講述一個尼日利亞女青年遭到了強奸,她找來了七位男性證人,卻仍然被伊斯蘭宗教法庭判得180下鞭笞。老板在剪報空白處給曼吉留了言:“伊莎德,遲早你得給我講清楚,這些瘋狂行徑、這些對女性的殘害,如何同你的穆斯林信仰并行不悖。”
當時,曼吉回憶道,她很有遭到歧視的感覺,但冷靜一番之后,她認為這也算老板承認她的成熟和智力的一種方式。然而,老板的挑戰仍然給她造成了不小的困擾,她不能把同樣的問題拿去問她的穆斯林同胞,那樣她會被視為叛徒。
但她到底還是發問了,在她的書中,在她的網站上。她還在網上發起了“伊智提哈德計劃”,期待建立全球最大的開明穆斯林及其盟友的網絡,以推動世人從人權角度審視伊斯蘭問題,而不是簡單地把伊斯蘭和恐怖主義聯系在一起。
《紐約時報》于是把曼吉和歐洲歷史上宗教改革的領袖馬丁?路德相提并論,但是,曼吉本人卻并不領情,她說:“這說法讓我兩眼發直、渾身發抖;好像我這樣的人,正企圖在新世紀里顛覆伊斯蘭。”
她收到了死亡恐嚇,一些看來只是嚇唬人,一些也許真的會要命。她停用了手機,因為全球定位系統會通過手機信號暴露她的行蹤,大型活動她也一律安排了保安。但是她說,這些措施,并不是因為她怕死,就算讓她明天就拜拜她也問心無愧;她這樣做,是為了爭取生存的時間,為了在離開之前,說完她想說的話。
曼吉坦言,自己所面對的死亡威脅讓前任女友頗感壓力。盡管前女友竭力克服了這種不安,但曼吉沒日沒夜、終年無休的工作時間仍然導致了她們最后的分手。“我不得不在私人生活和人生使命之間作出選擇,我不想讓這聽起來很夸張,但我很清楚自己被放到這世上來是為什么。我真誠地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是蒙召降世、承命而來的。所以,哪怕我的奮斗到頭來僅僅成為真正的改革者所書寫的歷史的注腳,那也很好。”

曼吉和母親較為親近,但在她看來,母親遠非她的港灣。“每個人都希望母親是自己的英雄和榜樣,但我的母親從前不是,現在也仍然不是。”曼吉寫作《伊斯蘭問題》時,母親憂心忡忡地告誡她不可觸犯真主。曼吉解釋說戳穿那些道貌岸然的教長阿訇并非對真主的不敬,母親絲毫聽不進去。書出版后,母親在清真寺做禮拜時遭到了阿訇的訓斥,等到禮拜結束后,眾教友前來表示支持,說她女兒所言極是,母親這才稍有釋懷。曼吉說,母親能轉變看法雖是好事,但她非要靠別人來告訴她孰是孰非,這一點,讓曼吉殊為抱憾。
現在,任教于大學的曼吉不時會發現自己的課上學生人數不如預期,她曾向一些女生詢問個中原委,得到的回答竟然是,有人群發匿名郵件,聲稱“要是讓我在那婊子的課上逮到你,你就死定了。”這種事,就發生在今日美國的高等學府。
當然,曼吉的理論也遠非無懈可擊,至少她對阿拉伯國家的籠統指責就很難使人信服。她似乎忽視了伊斯蘭世界內部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沒有看到即便在伊斯蘭教統治的區域,也有不少開明的思想和力量正在形成。而所謂部落主義,也不能完全歸咎于阿拉伯文化。曼吉的知識分子背景和她書中的一些近乎小報調侃似的散漫筆觸讓人感到了一種失衡。或許她希望以此拉近和讀者的距離,但這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整部著作的軟肋。
然而,瑕不掩瑜,曼吉所掀起的這場爭論生逢其時,而且她在書中與西方的一些文化多元主義的“謎思”針鋒相對,妙筆頻生。雖然她偶爾求全責備,偶爾狂熱偏執,但她為那些被迫緘聲的穆斯林吶喊,這不僅無可厚非,而且頗具膽識。畢竟,要想改變歷史的進程,挑戰是巨大的,但曼吉已經勇敢地邁出了第一步。














